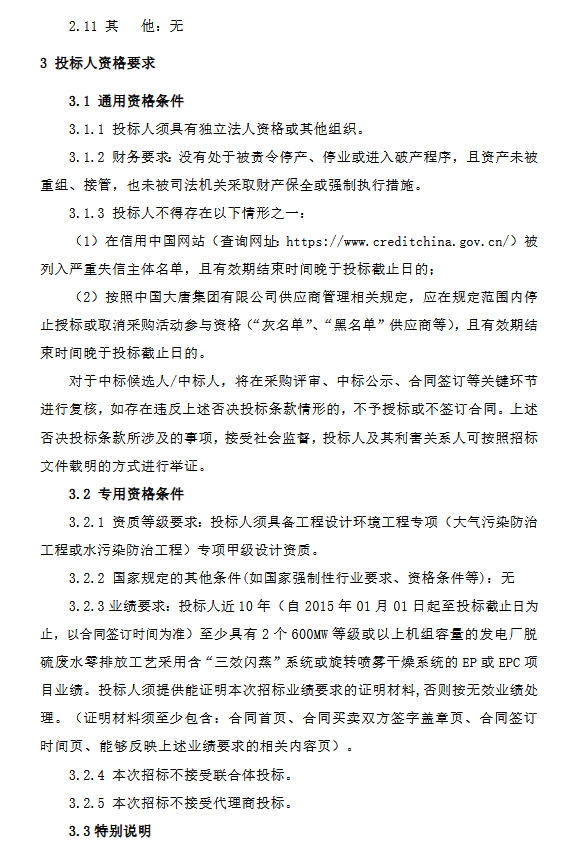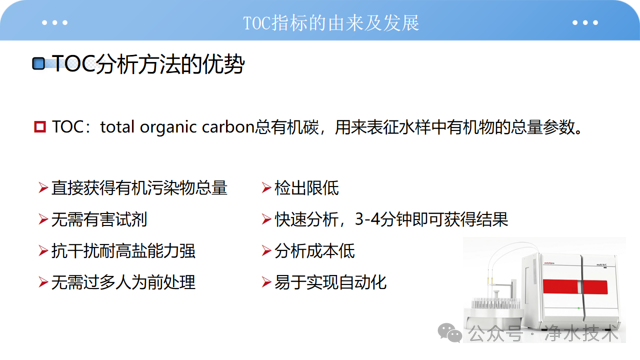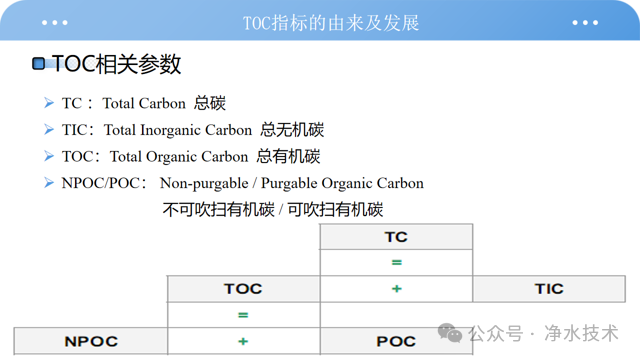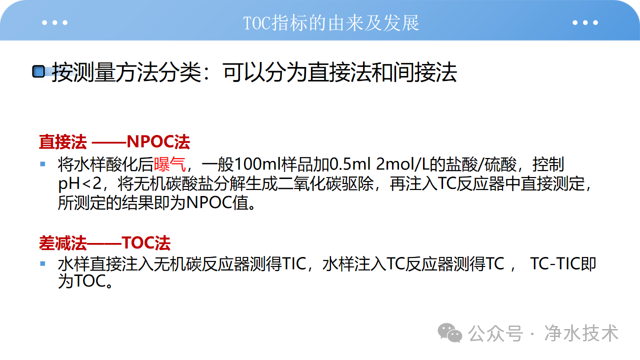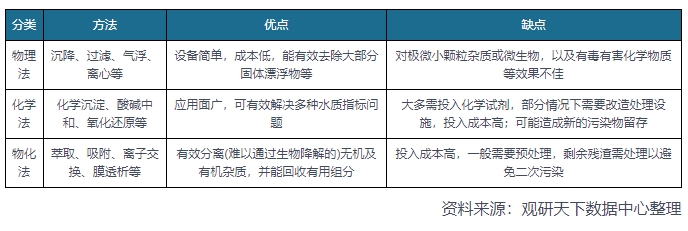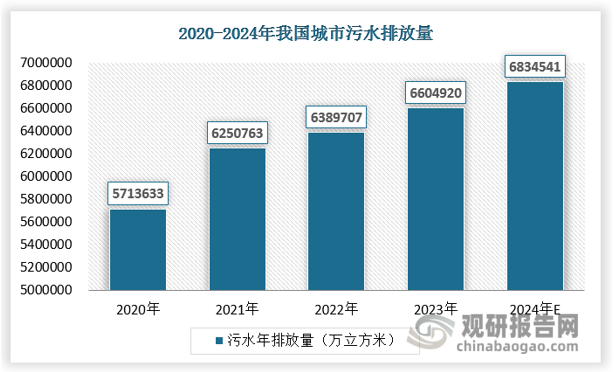年终盘点:投资大幕渐启 PPP仍待突围制度困境
慧聪水工业网 用PPP这个新事物作为一个增长点,那么从应然的、理想的层面来说,允许私人进入之前未开放的市场,允许企业承担公共职能,在网络、平台、共享经济的时代,在经济走向不乐观的时刻,PPP制度作为预算法的例外,如何真正起到对社会效率促进的应有作用呢?
PPP在2016年持续升温,不断地在公共经济部门吸引着眼球,热度甚至超过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今年PPP领域最热门主题是立法主导权之争,与之相关的各个部门互不相让,甚至连PPP该如何翻译,乃至内在涵义、外延范围也“一词各表”,即便是国务院法制办已被指定牵头负责立法之后,不同部门在10月份仍然几乎同时发布各自的部门规章。按相关部门的文件颁发速度和数量,从规范性文件上说,PPP已俨然成了一个成长和进化速度最快的法律领域。
但是,在各部门、参与者们埋头苦干,各种规则在一片欣欣向荣中产生和蔓延,许多案例和实践已经开始落地开花之时,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根本性的、系统性的制度和法律原则得到了真正的对待和反思。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不禁需要发问:凭借着花拳绣腿,我们真的有能力、有知识去处理即将到来的问题吗?
热潮背后的规则争议
说起来很深奥,但其实并不复杂,PPP就是政府允许私人投资和经营本来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领域。本来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因为管理的科学和专业需要,或者因为开放市场的需要,由私人来加以提供。
公私领域的商业活动,本来应当遵循不同的规则,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合理定价(价格规制)、普遍服务(无歧视性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自由接入(依赖于基础设施的上下游企业应当自由接驳服务),以及充分的信息公开(从治理到财务)和公开问责(解释说明并承担不利的经济后果)。因此,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在英国被称之为自愿部门,意思是本来是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自愿承担公共义务,当然也获得一个相对合理但是预期稳定的收益。
往狭义里说,PPP还可以分为不同模式,按照“谁出钱”来划分,可以分为公共服务外包(公共部门出钱,私人部门干活)和私人资金进入(私人部门出钱,私人部门干活)。就目前而言,财政部强调更多的是前者,而国家发改委的视角更多靠近后者。不同部门坚持自己的意见本无可厚非,有观点争论也是好事,但最近各自颁布的规则都在排斥对方的标准。
不管是哪一种PPP模式,资金、技术、人员等进入公共领域,都要依据公共领域的规则行事。但是,私人需要获得收益才会有激励,因此需要以合同的方式来确定对价,这也被称之为“合同方式的规制”。因为私人进入的领域不同,而采用的合作方式,可能在出资人、融资方式(股权、债券等各种不同的组合和比例)、运营方式(控制、管理、具体的财务和技术的权力分配)、回报方式、考核指标、中途和期末退出方式上,存在着丰富多变的实践。现在国内的讨论,似乎在具体实践的展开上花费了太多精力,而对公共商业应当遵循的原则,在现有的法律文本下出现了分歧。对这种合同方式的规制,讨论被简化成了定性问题:PPP合同究竟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这样的中国式分歧一直都存在,称为民行划分问题,比如按照刚刚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私人起诉政府,即便是商业活动,也要归为行政诉讼。这种归谁管的中国式争论通常会忽略一个问题,谁有能力管?法院行政庭通常缺乏合同裁判的知识,就算是归行政庭去管,恐怕也要从民一庭(民事庭)和民二庭(商事庭)借调人员才能解决。
有几个PPP机制似乎已经成了具体的争论前沿:发改委强调项目管理,用强制竞争性要约(CCT),即招投标来控制;财政部强调资金管理,用物有所值来进行控制。为推行自己的观点,各方都进行了各种论证,有世行专家介入,有国际经验比较,有既有案例的成功经验推广。在各部门眼中,这个制度不外乎几个核心共识:第一,要通过合同实现,各自推行了合同标准条款;第二,要保证“私”的部门进入者的收益,并且要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三,要由中央政府的审批部门控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扩张。
不可否认,PPP的确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的,符合国际趋势的方向。但需要看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一波又一波,各地纷纷搭建了融资平台,事实上似乎是播下了PPP的种子,但得到的果实则更多是“新名词套旧操作”。这期间,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原来的待审批项目重新包装,取得PPP的外衣,更有甚者,由国资委主动牵头联系地方政府,推动央企积极进入PPP领域。
类似种种,既是现有规则、认识的必然结果,也已然充分体现了“橘逾淮为枳”的制度产出能力的局限性。
各方为什么热衷PPP
抛开复杂的名词争议,追问一下:对于PPP,从业者为了其中的商业机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可以理解,各个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们这么热衷是何道理?事实上,现有的制度中的“新酒”,仔细看一下,不过是政府和私人签订合同完成合作、采用竞争性要约方式、审批和考核,每一环节以前都是存在的,甚至示范的合同条款都没有什么新意,“新酒”到底新在何处呢?
我认为,各方的动力在于可以利用PPP突破刚刚通过颁布的预算法。这部法律第三十五条拥有“突飞猛进”式的限权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除前款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
这一条文设置了四个核心限权:(1)地方政府不列赤字;(2)借债只能通过债券且程序复杂;(3)借债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4)地方政府不得提供担保。
法律产出结果是: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果岁入不足,又不能获得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发行公债比较困难,如何建设和运营呢?列入PPP就是一个必然选择,而且,监管部门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既然不能担保债务,那么就担保“流量”——收费基础设施上的“使用”,这就直接架空了预算法的限制。
预算法的本意是控权,然而用力过猛,催热了PPP,因为预算法的控权思路,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其标准理念中的政府,并不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政府不仅仅只承担行政、治安、军事、外交职能,更是广泛地参与着社会经济生活。但是预算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考虑的更大的政治原则:地方政府,不能有自己的空间和权力吗?地方利益,不也是我们的,甚至更接近于我们的利益吗?
这样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的法律制定和研究是相关的。每个部门法总是只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解释和制定规则。行政许可法把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解释为许可,忽略了经济法、环境法和社会法,预算法只知道控权,甚至忽略了宪法,当法律人也成为了埋头向下的专家,专家治国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考虑系统问题。
如何让PPP真正发挥效用
姑且承认这样骨感和悖论的现实,用PPP这个新事物作为一个增长点,那么从应然的、理想的层面来说,允许私人进入之前未开放的市场,允许企业承担公共职能,在网络、平台、共享经济的时代,在经济走向不乐观的时刻,PPP制度作为预算法的例外,如何真正起到对社会效率促进的应有作用呢?
PPP并不是新事物,且不说这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就尝试、探索的领域,过去在中国实际上也广泛存在着PPP实践。这是现在关注PPP的人们没有认真对待的:已有的经验,尤其是失败的经验。不是有个PPP的名字或者PPP的合同才是PPP,中国的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市场,交通部从1984年就开始探索了:高速公路,采用了经营权的概念,后来逐步因为交通国有企业的财力提高,私人逐步退出了。不光高速公路,长途客车经营权,以及近来非常受关注的出租车经营权,按照发改委的定义,跟PPP有什么区别吗?
经营权本质上是特许,也是PPP的一种。交通部最早推行的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法人制、合同制,不都是现在PPP的“旧酒”吗?出租车的经营权问题已经成为过街老鼠,连部长都明确提出要废除;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据说交通部在前几年曾邀请许多私人企业再次进入,但几乎无人响应。
假如发改委和财政部继续沿用现有的理解,无论哪一方占得上风,很可能几年后遇到交通部现在面临的局面。我毫无贬低交通部的意思,在短短30年取得的交通建设成就有目共睹,最早开放规制市场举风气之先,即便是网约车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也能从谏如流,这已经远超很多部委。但公私合作这件事情,历史摆在眼前身边,现在的PPP人熟视无睹,却非要炫弄各种新名词,从头学习。
本着久病成医的原则,不如建议一下,谁有能力和经验,交给谁负责如何?
回归正题,PPP要想真正起到促进社会效率的作用,需要在未来的规则中,根本性地解决几个原则性的“新知”和“新制”问题:
第一,合同法问题。如何理解这类合同,这些合同都是少则数年、长达30年的合同,有可能严格按照文本操作吗?长期合同在中国的合同法中如何解释,如何判断责任,一个连合同更改、变更、更新、修订都无法区分的合同法如何支持长期合同?当PPP人言辞振振地用民事还是行政去为这类合同定性时,有没有考虑过,谁从法律上处理过类似的争议?
举一个美国的案例,原告是一个有钱的汽车交易商,上世纪60年代,他愿意捐出一片土地给被告Erie县政府,建一座体育馆,用作美国棒球大联盟队伍的主场,以吸引人气,原告负责建设配套设施,双方可以分享由此带来的商业开发收益,但是最终招商引资失败,1971年县政府违约。案情曲折复杂,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PPP合同,原告寻求损害赔偿,官司从1971年开始,打了五轮,没错,在三审终审的美国打了五轮,到1994年才和解结案。在这期间,波斯纳、艾森伯格、戈登博格等法学权威纷纷登场发表意见,期间的理论争议不可胜数。这些问题,并不是有个合同文本就万事大吉了。
第二,用户和消费者问题。把PPP理解成为合同,现有讨论本质上都是一个:如何招商引资。可是一个问题被忽略了,PPP和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那么需求方、用户、消费者是不是这个法律关系的一个主体?他们应不应该、如何成为这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发改委和财政部把这个问题交给行业主管部门去规制,似乎没合同什么事。而在现实中,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比如那么多的PX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出租车行业引发的消费者怨气,解决的办法可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产品多中心供给体制。
第三,治理机制问题。对PPP是民事还是行政合同属性的定性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合同如何设计?合同只是一个通道、方式、表现,是叫合同、规定、经营权、特许权、股权并不重要,重要是采用何种机制让几方主体持续合作起来。如何筛选愿意提供公共产品的负责守信的人,这不是用价格机制就能解决的;如何确保产品或者服务在经营中不走样、最经济,而不只是出于防腐的拍卖、招标和事后的监督就够了的。
第四,政府的信用问题。这个问题恐怕是最难解决的,政府违约的情形并不都是恶意的,也可能是因形势变化而产生了需要。
同样,远的有1837年美国的经典案例,原告组成了公司,1785年获得麻州议会的特许,在波士顿查尔斯河上建桥收费,租约40年,期满后可以再延长30年。后来被告也组建公司并获得了特许,建了Warren,后者更方便,前者客源流失,原告遂状告麻州议会和Warren桥公司,侵害了他们的合同。历经近十年,原告在最高法院最终败诉,理由是该公司无权独占查尔斯河。首席大法官塔尼判决,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允许独占,公众利益高于任何一个单独公司的利益,并非侵害合同利益。
类似的案例在中国也有,故事是这样的,1987年开始通车的深圳梧桐山公路隧道是当时连接盐田区和深圳市中心的唯一通道。每次穿越隧道,一个来回需要20元。深圳市政府与梧桐山隧道公司长达九年的回购谈判,因为要价太高未果,于是决定在梧桐山隧道的上方山腰开凿一条新的隧道——深盐二通道,免费通行。面对大量车辆即将减少的现实,梧桐山隧道公司最终在深盐二通道通车前夕,不得不放弃高额叫价,将隧道交回深圳市政府。
这些有正当性的违约都历来是经济法上的困难命题,更何况因为人事更迭、政策变动、财政起伏而产生的故意违约呢?看看现实中只有国有企业有胆量进入一些领域,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现有规则和主张的结果吗?
总而言之,有关PPP的讨论,只能说刚刚开始,未来仍然是可期的。出路就在于按照应有的逻辑工作:先打好地基,建好承重墙,再去讨论装修是何种风格。
作者: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中心联席主任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