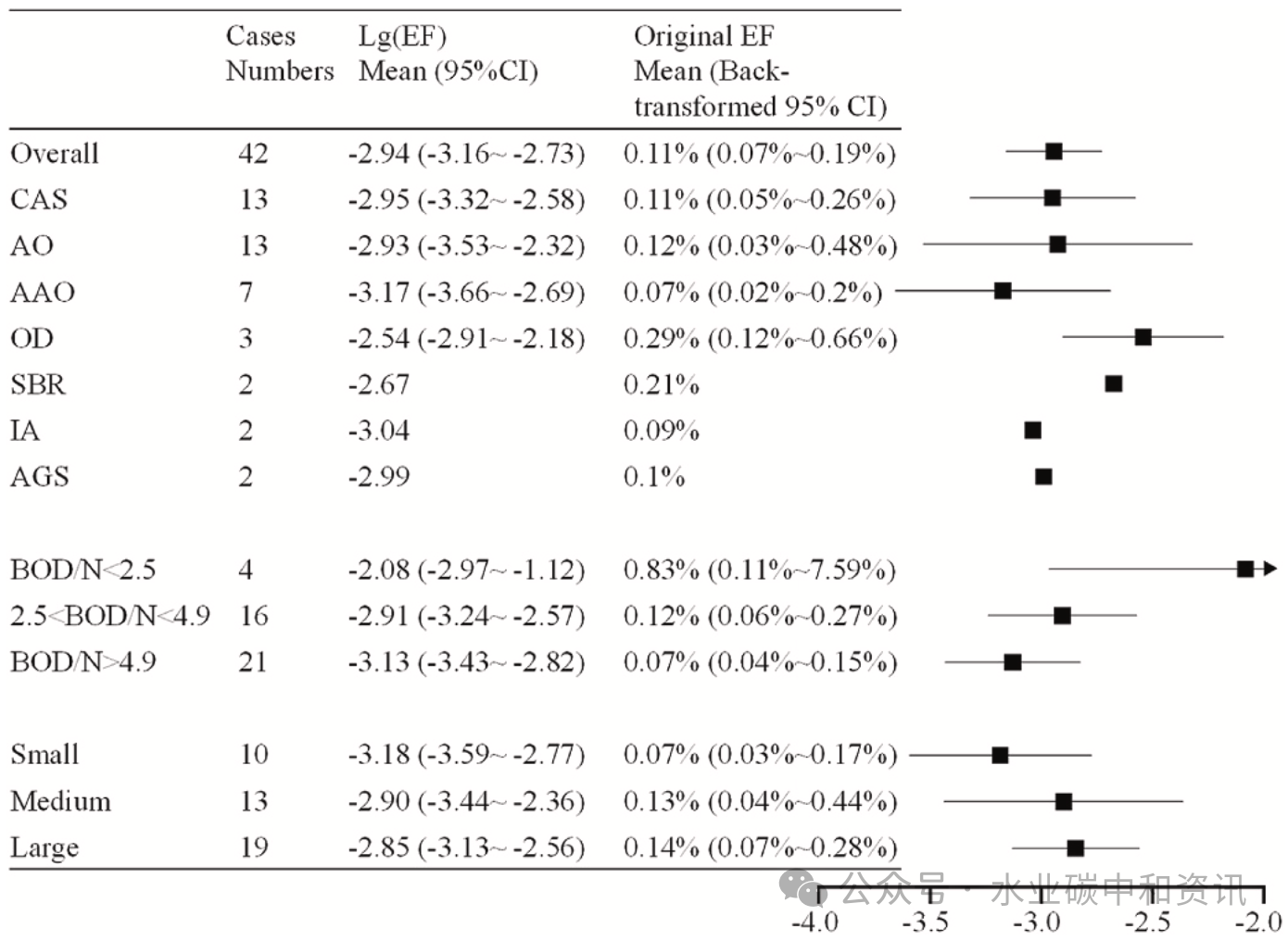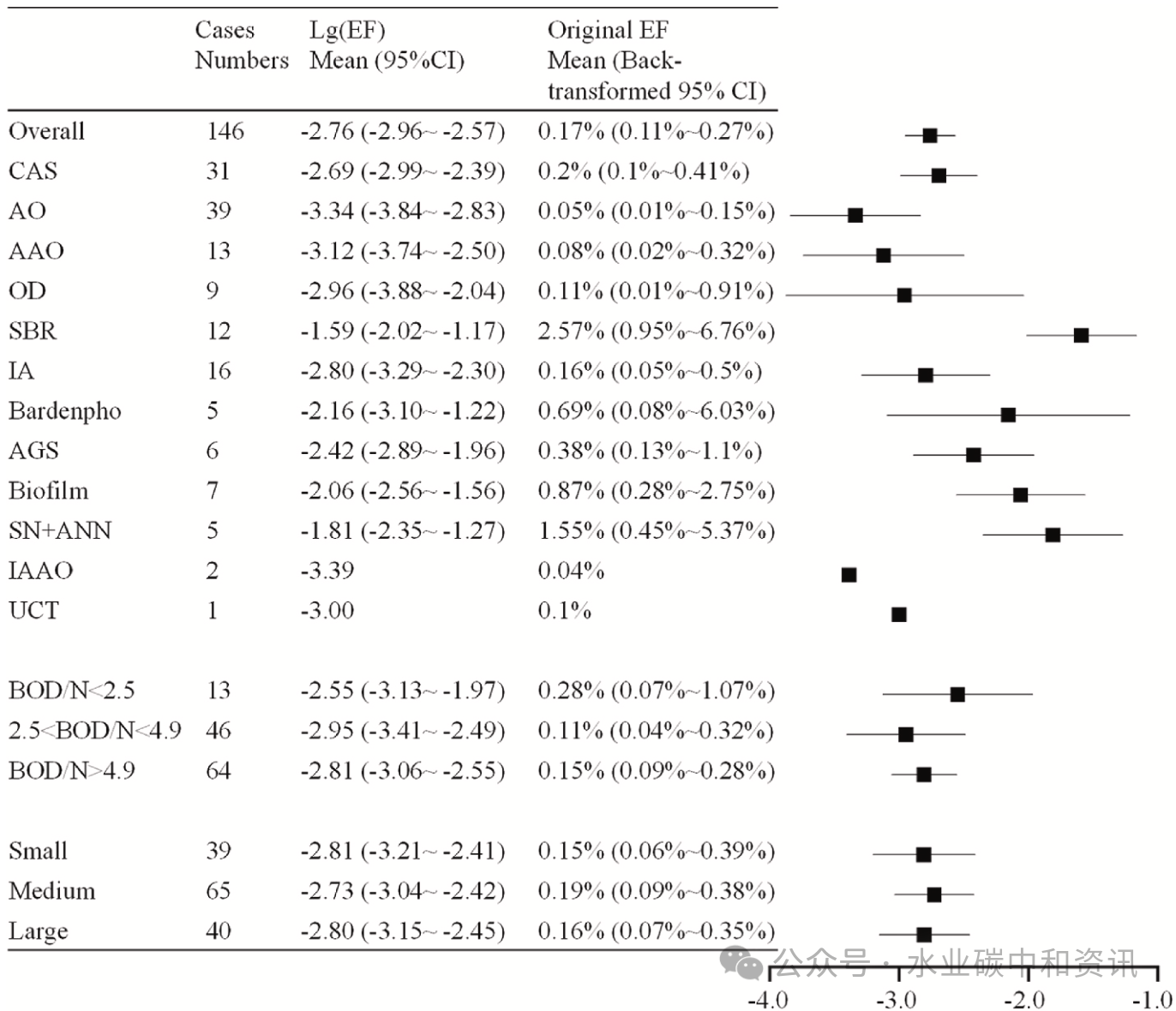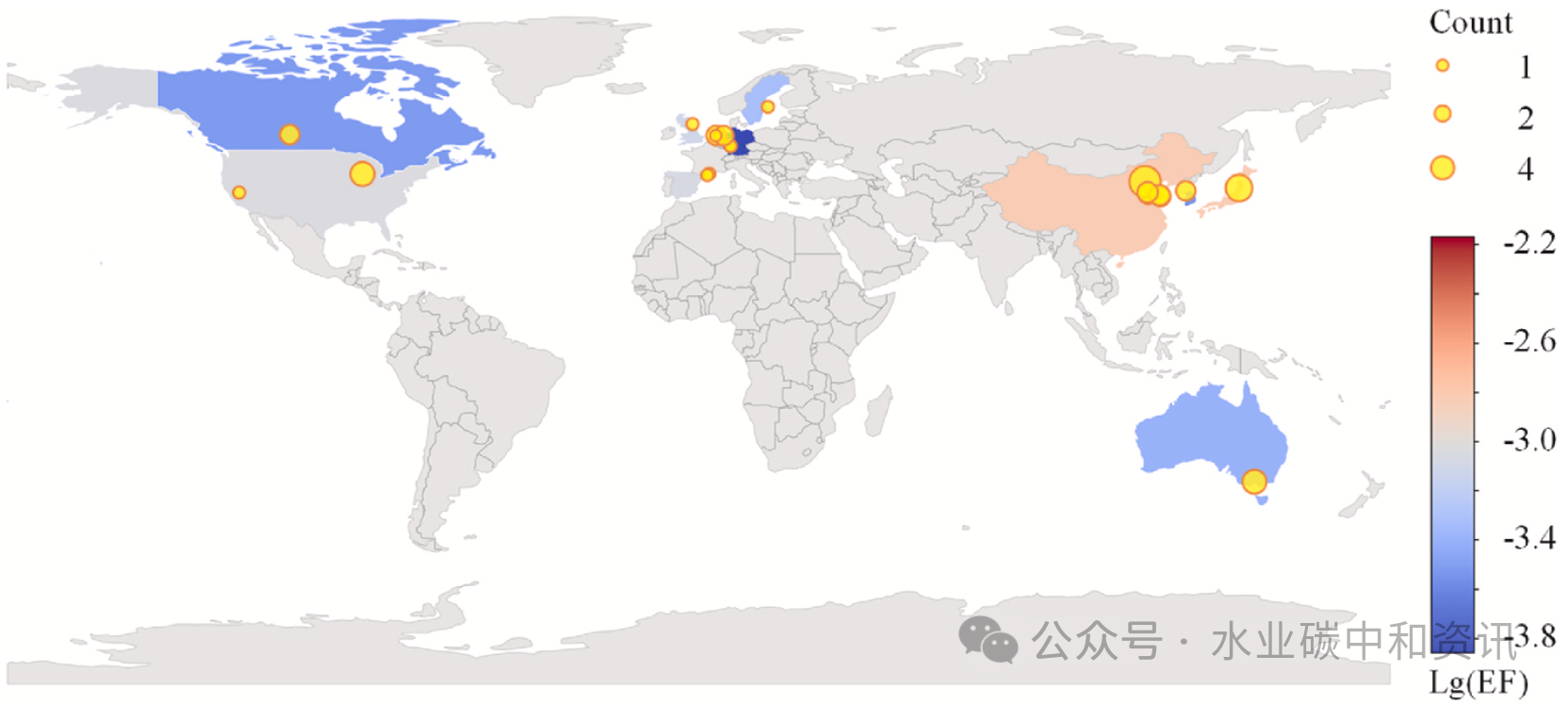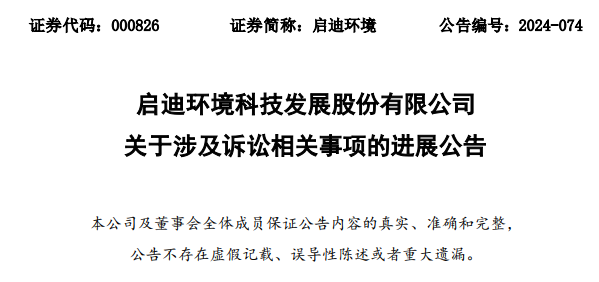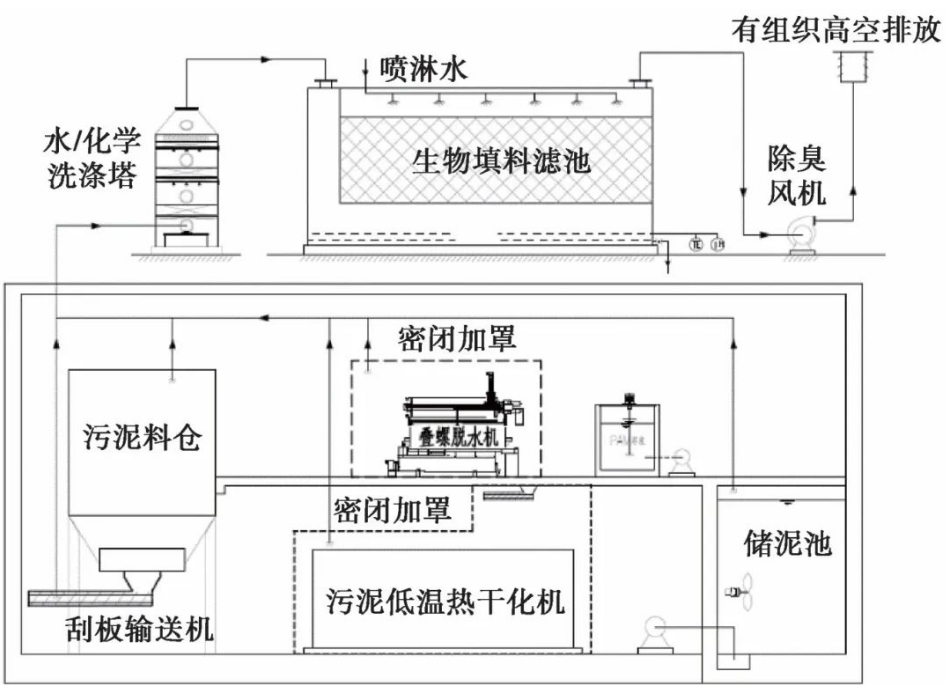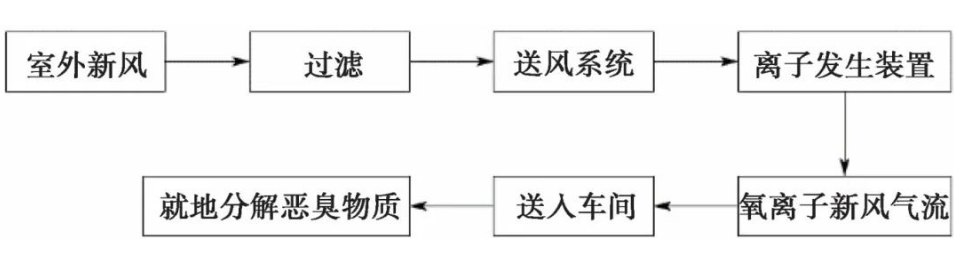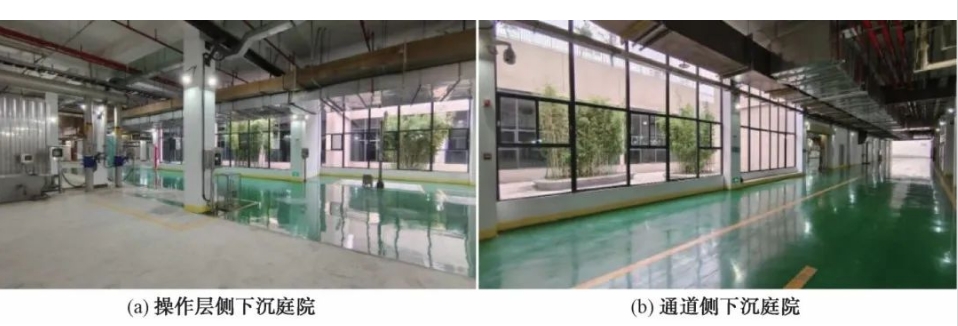当农村生态环境遭遇治理的危机!
慧聪水工业网 据权威部门三年前估算,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
“迫切需要治理”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普遍的面源污染,也就是已经深深植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过程的大量污染物排放,造成污水和垃圾触目可及。
二是乡村工业的点源污染,大量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质威胁到当地的农民生计和身体健康。
三是那些资源开采型乡村的生态破坏,严重者造成水源枯竭、土地沉陷、房屋坍塌,给当地居民带来生存危机,例如山西省的“采煤沉陷区”——近3000个村庄的200多万农民日夜生活在不安之中,8000多个村庄的近500万人因水资源破坏而“饮水困难”。
当然,三类问题在不少乡村是相互叠加的,而在第二、第三种类型的乡村,治理的迫切性更为突出,也带有“救灾”的意义。
就推进治理的进程而言,第一类问题是从2008年开始才真正被重视,多部委共同推进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连片整治示范区”的形式实施,投入的专项治理财政资金截至2013年大约为600亿元,而近期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三同时”制度和“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治理”的法律规范算起,治理是一直存在的,也是被不断强调的。
但是,大量的经验资料显示,着眼于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三同时”制度常常落空,许多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后果的企业也未担负起末端治理的责任。结果是在问题无法拖延时往往由“政府买单”,但是连同近期实施的农村综合环境整治一道,政府的“买单”既严重滞后,又因为治理过程中的“跑冒滴漏”而造成许多工程半途而废,或项目建成后无法运行。在笔者近年来重点考察的某能源大省,两项大规模的治理工程就呈现出这类状况。
比如,国家曾在2003年规定用3年时间完成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的治理,但该省直到2006年才真正付诸实施,而从2011年宣布“完工”后的情况来看,覆盖的目标人口(60万人)不到原计划的75%。与此同时,2007年启动的对“地方煤矿沉陷区”中676个“采矿权灭失村”的集中治理,在2009年初宣布“收尾”时,实际解决的只有305个村,其余371个村庄何时治理再无下文。结果在中央号召“采煤沉陷区治理”十年之后,该省的许多沉陷村仍处于“求救”状态,比如某区报告有71个村的农民需要搬迁,但真正搬迁了的不到一半,许多村民只能自行避难。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些“治理”过的沉陷村仍然将“新村”建在采空区上,偷工减料则使新房成了危房;一些沉陷村的“治理”以让工程承包者开采当地的煤炭为交换条件,造成原先未破坏的耕地成了露天采煤场,救灾变成了“造灾”。
另一个例子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该省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连片整治示范省”,计划投入1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占一半),整治1200个村,村均投入125万元。但从近期调查来看,在超出计划期限一年多之后,许多村庄的治污设施仍未完工,有的甚至尚未动工,有些已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成了“摆设”,原因是管网铺设不到位,污水进不了收集站,仍然是直接排放。以某示范区涉及的11个村为例,目前只有乡政府所在村建成了污水处理站,但是已建成的污水处理站却房门紧锁、门窗玻璃已被打碎。
如此结局无法不被视作“治理危机”。透过其中的种种细节,能够发现诸多不应有的疏漏。治理危机的核心表现是缺少负责任主体,以营利为大的企业最在意的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支持”,而并不太在乎生态环境和其中的村民;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本身又缺少监督,为了财政收入、GDP以及个体的寻租,总是在监管对象面前闭上眼睛;至于经常被屏蔽的村民,既缺少知情权和保护环境以守卫乡土的意识,也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且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有效制衡,而名义上代表着村民利益的村干部,又恰恰可能是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先锋”。总之,市场、地方政府、社会的失灵相互交织、相互促动,结果是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失灵。大量的投资变成无效投资,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和破坏的速度,而环境问题的演变趋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客观而言,环境治理的困境不过是总体性治理危机的一部分,且是甚为重要的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总体性治理危机的大格局中来审视农村环境治理。而考虑到治理危机困扰着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已有20余年,我们理应进一步追问:能否在一个整体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的系统中实现对其中的子系统的修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必须首先修复整体性的乡村治理系统,目标未必是较为含混而又空疏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是体系的真正改善和能力的真正提升。
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不应否认在现行体制中有着现实可能性。既然“强政府”也是一个优势,那么以近两年表现出来的“反腐”决心和勇气,依靠周密而又接地气的“顶层设计”,从整顿吏治和拍打“满天飞的苍蝇”入手来修复目前的治理体系是可能的;在进一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保护体系和财政保障体系也是可能的;进而,将过于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归还给村民、社区和社会,以约束地方政府的任性也是可能的。这样,农村环境治理,以及整个中国的环境治理,才会具备从源头治理到末端治理所需要的社会条件。
分享按钮